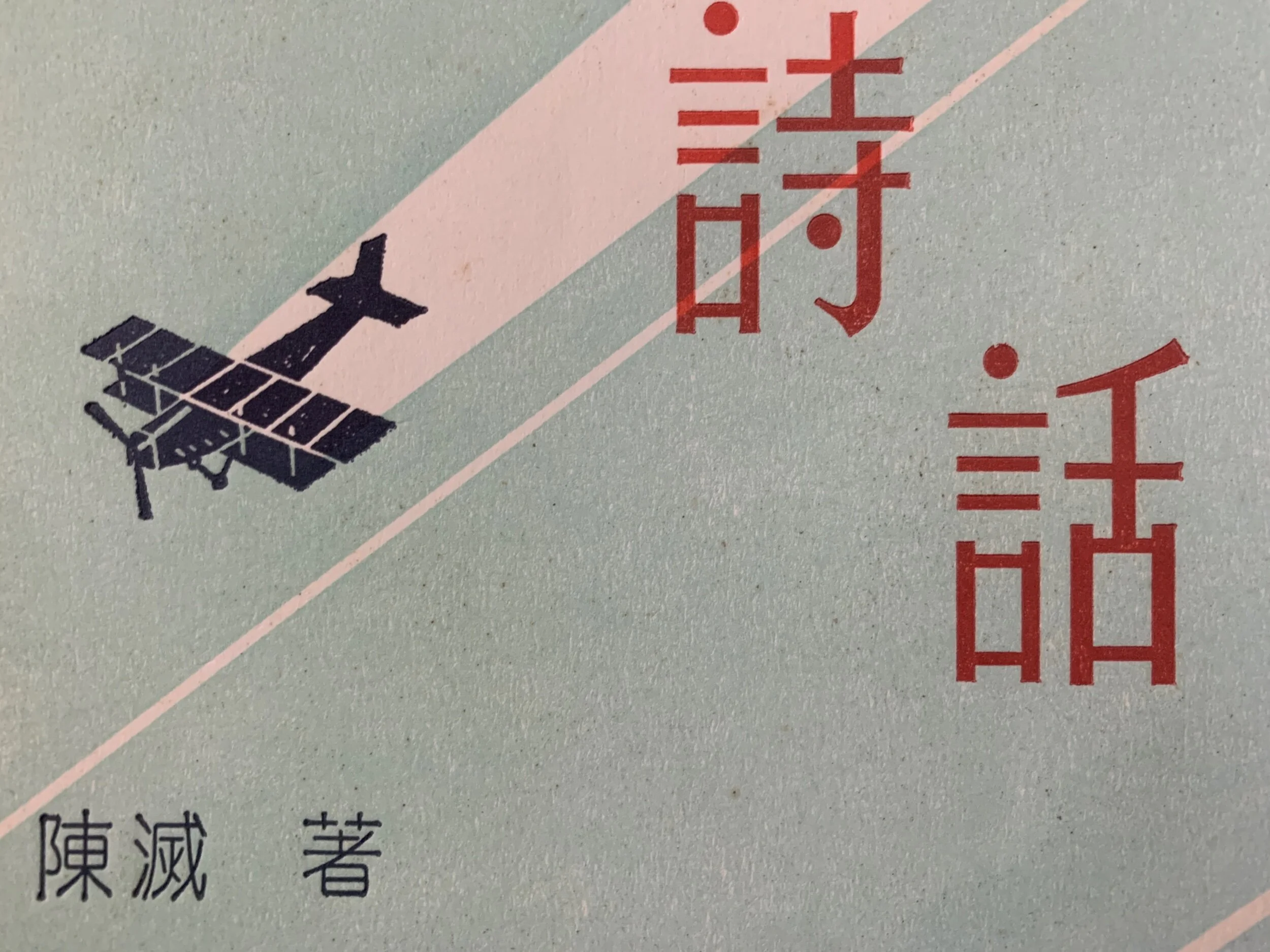所謂共同的意義,並不是社會上集體的聲音,而是我們身處這個後現代的時間: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中心。我們就同一議題下,道出自己的聲音。
《亂世破讀》書影
文/王曼懿
提到「亂世」,也許不論愛情還是其他的情感,腦海中浮現的畫面會是:有人在人群中突然奔跑着,看不清,逃離還是逃避我們想像不了的情況與關係。我們思緒盤纏附生,最後更可能會是無人留戀。
聯想「破讀」,一方面,如宋子江在序所言破讀是在其讀音中尋找短暫的解脫;另一方面,書中的每篇所破讀日常的意思,也「由音及義」融入我們生活的空間。
《亂世破讀》書影
我們活在碎片化的時代,停在這短暫的時間、急促的空間,「破讀」的意思讓我們平靜地把碎片拾起來,然後在這些碎片中,尋找共同的意義。所謂共同的意義,並不是社會上集體的聲音,而是我們身處這個後現代的時間: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中心。我們就同一議題下,道出自己的聲音。這中心,卻與書中提及我們個人的聲音在社會上如被吞噬般的微弱和有限。可是,這本書「破讀」的意義是非常強大的,書以文字與照片,以感性的文字去表達理性的思想,使讀者能從不同的層面去觀看。
正因為不停在碎片中尋找,在各碎片的關係中重復,事情不會因支離破碎而變得微小,這不穩定讓讀者思考自己與亂世的關係。我在法律學院的圖書館看畢《亂世破讀》這本書,沉默了。毫無違和感,我驚呆。
我特別喜歡的是〈生活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文中提及我們是在大混亂時代中,尋找令人信服的秩序。這就像拼著不同的碎片,甚至吻著看見或看不見的傷口,尋找完整。比較文學的核心在這本書完全呈現:以文學、藝術、電影和照片的形式,哲學的理論作支柱,和社會的關係。
〈高牆.雞蛋.馬拉松〉
陌路在前,不正只是高牆和雞蛋,還有馬拉松。書本亦提及不少其他的文學作品,以其去論述香港的社會情況。當中〈高牆.雞蛋.馬拉松〉,文中巧妙地將村上春樹的話語:「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與村上春樹為一個馬拉松愛好者作連繫,這兩片「碎片」正正把馬拉松的精神展現在雨傘運動上,亦借此提醒大眾,希望看見這兩項運動背後的意義是堅持,至今仍守著。
高牆和雞蛋這鮮明的比喻,強烈的對比。不只是一硬一軟、一高一低,也是強大和渺小。雨傘運動後,大部分人的焦點都在社會運動的場面、媒體的報導、引起的動盪,甚至想著帶領運動和參與者背後想要獲得個人利益。明瞭,在這以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商業城市,不難理解這普遍由上一代人帶來的價值:以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多數服從少數這個概念。
電影《危城》劇照
正如文中〈危城自危〉,所談及的是《危城》這部商業電影,正正帶出了如果追求公義是需要無辜的百姓付出代價,我們還有必要繼續追求嗎?意味着在這急速經濟為上
的時代,不要說是文學,很多人的一生只是為了溫飽和享樂,以「傳統」和「慣常」來包裝「愚昧」而妥協。〈被家具活埋的男人〉中提及卡夫卡的《審判》和《城堡》與迪米崔.舒塔奇斯的《錢已匯入你的戶頭》,共同的地方都是在談個人如何在社會體制中不斷地掙扎,只是處理的方式不一樣。我們的觀察是時代的轉變如何影響對待生活的態度,穩固與穩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即使在法律的層面上,如侵權法中,即使案情如先前的案例相近,審訊時也要看案件的事實,視乎各種因素包括整件案件的性質及情況而定,從而為其作出的決定,並不是只單靠先前的案例來作出判斷。
電影《一代宗師》劇照
《亂世破讀》把碎片化這個概念融合,告訴讀者別怕面對破碎的狀態,破碎也是全面的一種呈現。以《一代宗師》的名句作結:「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書讓讀者置身一個充滿碎片的世界,每篇均像一片碎片,以不同文學藝術領域去回應香港社會的面貌。如〈高牆.雞蛋.馬拉松〉與〈危城自危〉的篇章,以主流商業電影及文學藝術作品作依歸,大眾與小眾,帶出本土和日常在社會大事上的角色。全面的概念並不是與大眾所看見的一種完整,那只是很表面的理解──能在這亂世中,以破碎的方式來觀看和閱讀身邊的事物;非流於表面而用心去了解,明白破碎也是變成完整的一個過程,全面是有接納和包容不同聲音的意思。
作者簡介:王曼懿,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碩士,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攻讀法律博士。文章散見於《明報》、映畫手民及電影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