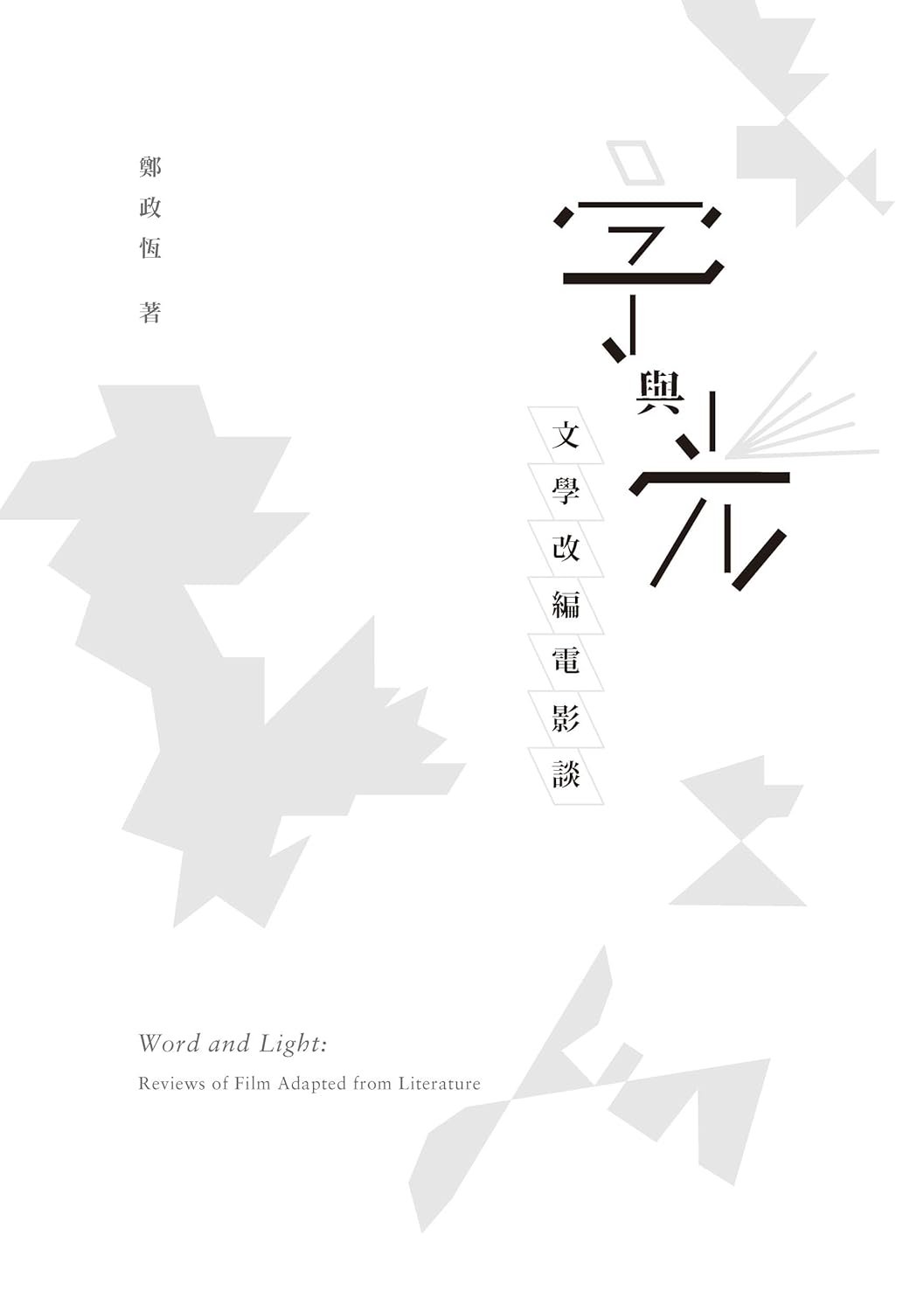作家、影評人鄭政恆先生榮獲第十九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家年獎 (文學藝術),在訪問中,鄭政恆先生不禁回想十二年前由也斯先生提名而獲得的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這次獲獎不單是對他在文學藝術界的貢獻作肯定,還提醒了他:文學藝術是踏入文化藝術領域的第一步。已出版三本詩集的鄭政恆先生近二十年對詩歌的熱情從未間斷,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詩歌研究,如在2020年與葉輝先生合編《香港文學大系 1950-1969:新詩卷二》。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的他,在2016年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在不同藝術媒介中遊走,寫出一篇又一篇尋幽探勝的文章。鄭政恆先生在訪問中談及最初接觸文學以至電影的時刻,十年如一日,談笑風生,文學的魅力依舊不變。
文:楊啟超
第十九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家年獎 (文學藝術)奬座。
「當初如何進入文學藝術的世界?」
鄭政恆先生當初先接觸金庸武俠小說,但當時未知自己會走上文學藝術之路,更未曾想過多年後會出版《金庸:從香港到世界》,成為研究金庸小說專著的編者。兒時更浸淫於《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文學,他說多年後作相關研究時,像見回老朋友一樣。文學就如無形的友人,陪讀者走到天涯海角。
「在這一刻,文學藝術對你來說是甚麼?」
鄭政恆先生認為文學藝術是十分自主和不功利的載體,也是距離消費主導社會比較遙遠和抽離的一個理想世界,透過文學可以去講述、表達和與世界對話。他說特別是在數據、流量主導和訊息萬變的現代,在文學的世界可以去作任何的自主選擇,不必受別人左右,以獨立、安靜和自主的姿態作閱讀,以及不受階級影響,或貧或富都是一視同仁。
「當初如何接觸影評和發現影評的美妙?可不可以推薦一些書籍給想寫影評的人?」
鄭政恆先生說自己是二十歲左右才認真接觸電影的,憶起當初接觸法國新浪潮導演尚盧·高達 ( Jean-Luc Godard ) 和瑞典導演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的電影時,帶給他思想上的衝擊和生活上新的感受,在別人的世界中獲取新的視角去看待事物,過去不斷發掘歐洲的電影大師,如法國、意大利、瑞典、蘇聯、俄羅斯、波蘭等等。問及近年喜歡的導演,他提及美國的Terrence Malick、韓國的李滄東。
鄭政恆先生推薦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反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給想寫影評的人,然後建議可以找一個與自己「同頻率」的導演,把他看待成一個作者,把主要的電影都看一遍,尋找出整體的風格和主題,譬如他在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探討現代人的疏離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鄭政恆先生稱透過電影,能讓自己與外邊世界有思想上的連結。
鄭政恆先生說只要有文學的價值,便可看待成一種文學,但他強調電影是綜合藝術,有時候電影劇本只是一種參考。
「現時網絡媒體盛行,影片文字並茂,你認為純文字的影評有甚麼難以取代的地方?」
先引用政恆先生在《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中寫的一段話:「在電影中看到甚麼就是甚麼,而文字的閱讀經驗是不同的,多了一重想像空間。」他認為文字能創造一個空間,比起吸睛和流量,讓讀者能夠細味咀嚼、深思文字背後的想法和觀點才彌足珍貴。他說現在寫影評少了一份「打入影評圈子的焦慮」,在自媒體的年代,每個人都能發表言論、百花齊放。
「在你心目中,電影劇本可唔可以作為一種文學?」
鄭政恆先生說只要有文學的價值,便可看待成一種文學,但他強調電影是綜合藝術,有時候電影劇本只是一種參考。可見研究一部電影要從多方面鑽研,如剪接、攝影、燈光、佈景、服裝、色彩等等,雖然電影本身的歷史相對不長,但當中的要素可以是過千年的,藝術的廣度和深度是可在一部電影慢慢雕琢和展現,當中更滲透時代精神、意識形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等。
鄭政恆先生論〈詩意的電影,詩的電影〉
《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香港 : 香港三聯,2016)
〈詩意的電影,詩的電影〉是鄭政恆先生的著作《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裏的一篇文章,從文學與電影的關係、詩意寫實主義、寫實主義、詩人拍攝電影和詩與前衛電影的關係等去探討詩與電影交流的可能性。
鄭政恆先生引用「詩人導演」尚・谷克多( Jena Cocteau) 和柏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對「詩的電影」的論述和觀點去為讀者提供廣闊視野,如講述谷克多認為「詩意只是表現手法的外在手段,而詩是內在的藝術產物」,鄭政恆先生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和超現實主義去概括谷克多電影中的風格、影像和象徵。另外,鄭政恆先生引用了柏索里尼的論文《詩的電影》( The Cinema of Poetry, 1965),提及電影語言和書面語言的不同,電影中的形象符號(im-signs)既主觀又客觀,除了傳統的敍事手法,電影導演能以各手段和技術帶觀眾進入其世界觀所構成的「詩的世界」。
文章的最後以詩與前衛電影討論「詩的電影」。在五、六十年代興起的美國前衛電影中,導演們所運用的電影技巧及其風格和形式為「詩的電影」作延伸。鄭政恆先生以史丹.布力奇治(Stan Brakhage)的電影《狗.星.人》中貫穿的主題刻畫出詩的電影的內涵,及引述奇治的著作《視覺隱喻》中的「太初之道」帶出其電影中的理論實踐。另外,鄭政恆先生還以詩人龐德的意像主義詩論連結布力奇治的電影。不論是詩或電影的可能性還是有很大空間待發掘,正如文章最後一句話:「為貧乏的時代加入新的語言、新的思想。」
鄭政恆先生把對文學的熱愛帶到學術研究上,以文學、藝術、電影、學家論述等開拓新話題,為讀者和有興趣研究的人開闊視野、順藤摸瓜、左右逢源。恭喜鄭政恆先生榮獲第十九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家年獎 (文學藝術),實至名歸!
本文作者(右)和鄭政恆先生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