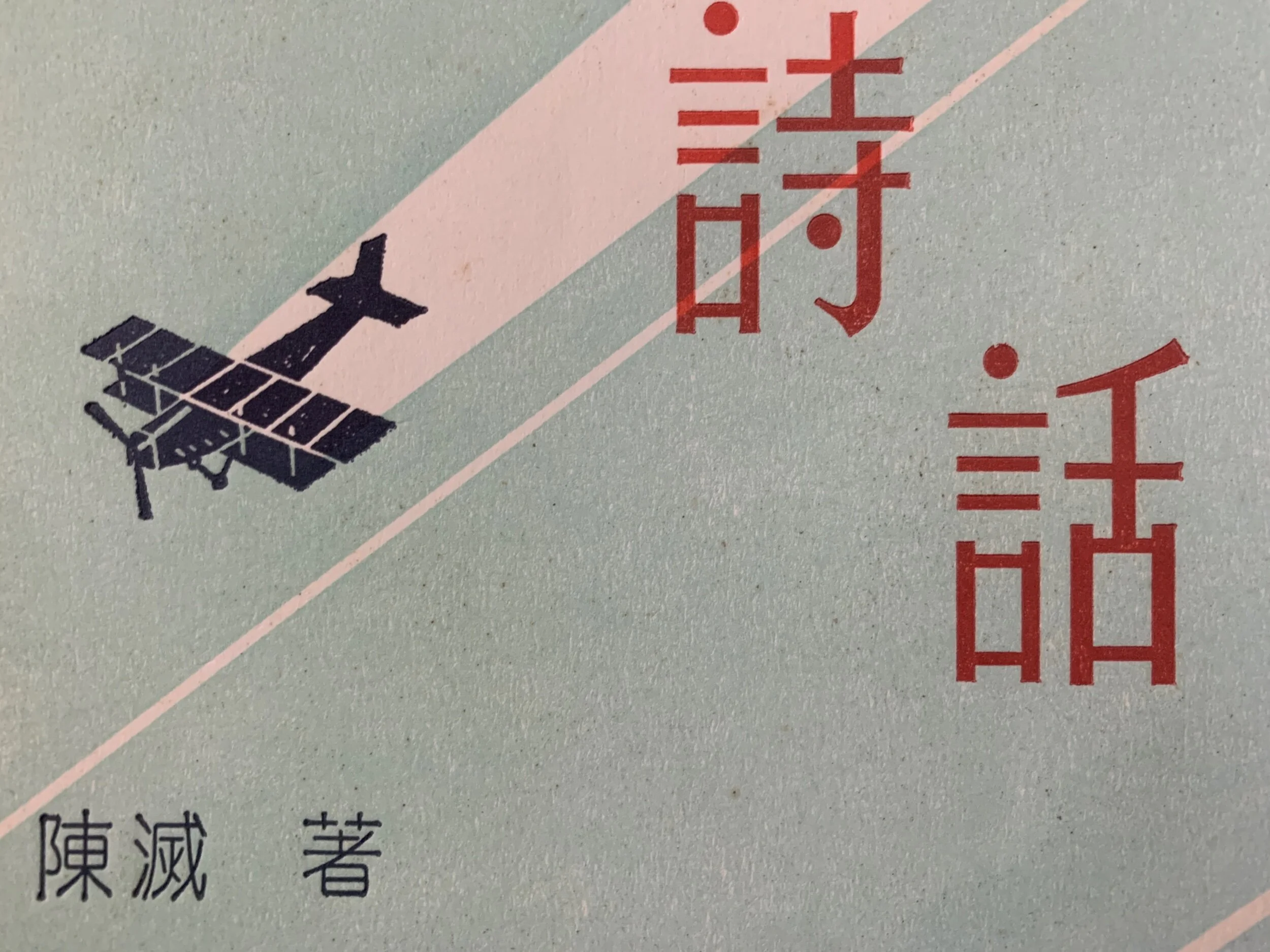這種不安、驚慌、無助、奇詭陰森的暗色調,在《明媚如是》時彷彿像相片後製的調光功能,整體的色度明亮了,由激烈深刻的刺痛,變成輕描淡寫的重量。
《明媚如是》書影
文/周怡玲
起初知道「梁莉姿」這個人,是她以「白懿」為筆名寫詩的時候,一位橫掃多項文學獎的少女;後來真正見面,已是幾年後的一個訪問,那時的她,正準備出版第一本詩集《雜音標本》;真正讀她的小說,卻是近來的事。如果說第一本小說集《住在安全島上的人》是她書寫疼痛、各種嘗試和摸索的階段,《雜音標本》是拒絕定型、收集和記錄各種聲音,那麼《明媚如是》就是她開始找到自己的聲音。
《住在安全島上的人》的名字取得很好,既名「安全」島,但一點也不安全,書中各篇小說的主角都在狹小的空間壓縮自己、異化自己,在短暫尋找個體生命後,繼續委屈自己,漸漸變成集體所期許的樣子。這種不安、驚慌、無助、奇詭陰森的暗色調,在《明媚如是》時彷彿像相片後製的調光功能,整體的色度明亮了,由激烈深刻的刺痛,變成輕描淡寫的重量。從第一章節中〈皮鞋〉和〈貪生〉兩篇小說主角的自殺,漸漸到全書最後一篇〈林微和慧珍樓〉,沉重和壓抑的程度漸漸減少,也慢慢地像清晨時份由漆黑一片到透出一絲柔和的陽光,全書最後一段既是該篇小說的結尾,也是全書作結,十分有巧思:「陽光不溫不烈,一切明媚如是。」面對自身、社會環境各種變遷,梁莉姿筆下的主角都在努力生存,好不容易捱過一天,新一天又重新開始,到底是希望,還是生活只是一切依舊,似乎是個開放式的結局。
這種明媚/不明媚的矛盾也伸延到書封面的設計,用上奪目的鮮黃為主色,中央部分則有黑雲在多條白間中透出來,彷彿一早已在封面時就隱隱告訴讀者,看似陽光明媚、充滿希望,卻同時有黑雲並生,所有事情不是絕對的光與暗、黑與白、是非分明,而是光明處必有黑暗,兩者雙生並存。而這種思維亦貫穿書中的角色,小說中的主角就像一對「雙生兒」,其中一個角色柔弱、不起眼,另一個角色稜角分明、耀眼奪目,既互相矛盾,又互相呼應。例如〈群〉的阿群和明微是情侶,明微會不平則鳴,為了很想得到的東西而努力爭取,而阿群怯於表達自己,從來沒有強烈的欲望;像〈雙雙〉的「他」和阿細,「他」沒有學歷,十多歲便開始從事勞動工作,只求生存,對身邊的事情不慍不火,同母異父但以甥舅相稱的弟弟阿細大學畢業後搞社會運動;又如〈球賽〉的林微和詹國生,詹國生教懂林微世界的樣子、什麼是公義,卻在現實的抗爭中退縮,林微透過詹國生認識世界,反而能夠義無反顧地爭取;還有〈林微和慧珍樓〉的「我」出生後住在唐樓「慧珍樓」,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表妹林微從美國到港暫住在慧珍樓,是名「American girl」坐不定、愛冒險,常常帶「我」四處搗蛋,九七後二人處境對調,像個交叉,「我」到美國讀書,而林微長住香港;〈皮鞋〉的「我」成績一直不好,經常失眠、嘔吐、焦慮,努力適應學校生活,班長是眾人眼中的好學生,品學兼優,沒人想到她同樣承受很大壓力,最終選擇自殺也沒人理解等等。梁莉姿筆下的他們,沒有對與錯,反而更像是在呈現出在衝突過程、眾多聲音中,柔弱的一方對另一方的逐漸理解;可惜在生活、時局變化中,角色仍無法走出困頓,「醒悟」同時,也帶來無力感與遊離。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事件發生,怎樣回應很值得關注。梁莉姿寫作這十篇小說的時候,香港正接二連三發生社會運動,見證著時局變遷、各種社會矛盾、不同立場的人互相針鋒相對、分化,令她有更多的無力感,亦使她開始留意不同立場的人的聲音,讓自己和讀者嘗試透過小說了解和接受對立的一方行為背後的原因,如張愛玲所寫:「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她筆下的小說從以前的反抗、壓抑,變成現在的理解、接納,對這位備受矚目的年輕作家來說是個人和寫作的成長,令人不禁有點期待她日後的作品呢。
作者簡介,周怡玲,現職編輯,沒有想像就不能活下去,所以很喜歡文學。